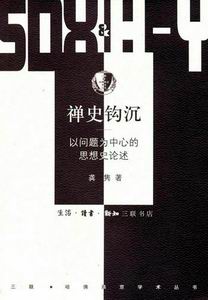 《禅史钩沉: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论述》,龚隽著,三联书店2006年8月版,26.00元
《禅史钩沉: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论述》,龚隽著,三联书店2006年8月版,26.00元
台湾学者林镇国对本书给予高度评价:“本书的研究针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汉语禅学
开创“范式”与否,自要留待后人追认。不过本书还真的包含了对葛兆光的批评,虽然只是在一个不易发现的注解里:“葛氏的问题在于,当他寄希望于禅学思想史能以‘顺着讲’的方式,去‘消解我们的立场’,还原出‘古人的理路’和不‘带有任何出自现代观念的偏向’的‘忠实当时的历史’时,他又回到了他批评过的那种历史知识的本质主义的客观性中。”(第7页)――虽然它在本书的文脉里是针对葛兆光的《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一书而发,但我们不妨以后者的成熟之作《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为蓝本,看看这个貌似轻描淡写、实则批亢捣虚的评语是否成立。
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一书的基本见解是:“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该书第14页)――但他或许没有想过,他所谓“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其实预设了一个重要的前提,亦即不同类型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在某种基础层面上的“可通约性”。否则,正如把一头牛和一匹马的平均值当成是半头牛和半匹马是没有意义的一样,谈论彼此不可通约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的平均值也是毫无意义的。
既然有此“可通约性”的前提亘于胸中,葛兆光从福柯向年鉴史学的跳跃就不可避免了:“年鉴史学的‘长时段’说,并不像福柯那么坚决地拒绝连续性追寻,而是依然试图描述历史变化的轨迹,只不过,它所依据的时间标尺不再是过去的王朝变动与政治变动,而是缓慢却又深刻地镶嵌于历史中的生活样式的变化……我想,在思想史研究中,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正好用这种‘长时段’来描述,因为它也是缓慢地但又是连续地在变化,真正地构成思想史的基盘和底线。”(同上,第17~18页)――这个“基盘和底线”的比喻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为什么思想史就得有“基盘和底线”?答曰:“思想脱离知识系统的支持,将失去语境。”(同上,第33页)――倘若果真如此,那么主体间的意义交流过程大概就可以概括成如下形式:从某甲的“知识系统”中产生了一个“思想”,传达给某乙,某乙再把该“思想”纳入自己的“知识系统”――但“知识系统”难道不是只在公共的、“平均值”的层面上才成立吗?它又如何能被某甲和某乙这样的个体内在化?事实上,主体间的意义交流过程更可能是这样的:某甲产生了一个“思想1”,在公共的“知识系统”中编码后传达给某乙,某乙再将其解码成“思想2”,而由于编码和解码未必遵循相同的规则,“思想1”和“思想2”可能相去甚远――也就是说,知识系统对思想不是起支持作用,而是起中介作用,但这种中介作用能否为葛兆光主张的“连续性”提供担保呢?只要谁还记得盲人摸象的故事,答案就不言自明了。
葛兆光还对如下图景表示不满:“人们在叙述思想史或哲学史的时候,想象着思想与学术的薪火,不绝如缕地在这些圣哲身上相传续,在普遍的愚昧中,他们惨淡经营,小心地呵护着文明的火种。”(同上,第175页)――问题是,这段话里其实提到了两幅图景,一幅是薪火传续,另一幅是呵护火种。葛兆光可以否认历史上存在过某种薪火传续的谱系,但他真的能否认少数人呵护文明火种的真实性吗?即使我们承认周敦颐“宋儒之首”的地位出自后世朱熹等人的表彰,但这难道就意味着可以把他和他的《太极图》贬到江湖术士的层次吗?对后世编排的薪火传续谱系的质疑,难道不正应该使我们直面思想之火在不同介质之间的真实蔓延过程,而不是犬儒主义地把火种和黑暗等量齐观吗?当然,倘若一定要在广漠的黑暗和星点火种之间取一个“平均值”的话,结果也无非只是黑暗,可是,这种横向地在一簇不可通约的对象之间取平均值的做法,和那种纵向地为一簇对象编排谱系的做法相比,又有什么质的区别呢?
在“平均值”观念的误导下,葛兆光的思想史研究完全倚重于“外缘性”的解释路径:“……‘平均值’和‘精英思想的背景或土壤’,实际上是社会史中的一部分,思想与社会的关系是很深的,如果我们注意这些背景,那么,类书、课本、历书、戏曲小说、平庸的东西、常识性知识,都可以进来了。”(同上,第125页)而《禅史钩沉》的价值恰恰就在于有意识地超越这种“外缘性”解释路径。作者指出:“问题本身对于方法的择定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如经验世界的社会思想问题或许更切近于外缘性的解释,而纯粹观念性问题,特别是形而上学问题,与其还原到社会存在的一般条件和实证性层面来分析,不如顺其内在理路和知识的自主性延伸来加以考释。我们就很难完全从外缘性的解释来说明康德批判哲学的转向,正如他自己表白的,是哲学史上的休谟问题使他从独断论的迷雾中惊醒过来,这显然更多地要从哲学观念内在的自主性脉络中,才能求得恰当的理解。”(本书第34~35页)
这里所说的“从哲学观念内在的自主性脉络中”上下求索,并不意味着回到福柯以前的那种内在观念论的思想史研究视角。作者批评说:“通过语词的相近、逻辑命题的相关性来说明陈述意义的同质性和所谓思想史解释的‘内在关联’,几乎成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般范式。这一范式常常过于简单地把某些特殊事件、思想联系到一种统一性的历史流程中,忽视问题本身的异质性。”(第33页)――那么,作者对“哲学观念内在的自主性脉络”的切入,又是如何在摒弃了内在观念论的前提下得以实现的呢?这有赖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那个似乎已经被国人谈滥,但其实很少真正引起共鸣的观念:“家族相似”。“从思想史的意义上说,相同的语言、概念、命题之间,并非完全表达意义相同的陈述,但也不是完全无关的意义陈述,它的统一是在以‘家族相似’,而不是单一本质的意义上得到理解的。因此,相同的句子、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在思想史的不同场景中,既存在断裂,也存在关联。这一方法没有推翻而是修正了传统思想中过于简单的连续性观念。”(第36页)
以僧肇研究为例,“由于《肇论》中广泛应用到老、庄、玄学的语词和相关的一些命题,因而使学术界一致认定,僧肇是在道家、玄学化的系统中来完成印度中观思想的,甚至说僧肇思想属于中国道、玄思想的内在系统。”(第33页)作者却以无厚入有间:“《肇论》的道、玄化究竟是从形式的系统(如语词等),还是从实质的系统(义理)出发?况且,语词的沿袭是否必然意味着义理的承接?如果照吕?所说,《肇论》的形式和实质二者皆存在道玄化的问题,那么又如何进一步解释僧肇对他之前中国般若玄学化‘异端之论’的批判匡正和超越?”(第95页)这种提问方式正是对前述“家族相似”观念的具体应用。
有此视角和方法的显著更新,本书自非詹詹小言。除对僧肇的研究以外,作者还在书中论述了从“印度禅”到“中国禅”的演变过程、禅风“尊戒”与“慢戒”的关系、中国早期禅的顿渐、中国禅宗历史上的“方便通经”、“念佛禅”、宋代“文字禅”、唐宋僧和传灯录对理想禅师形象的不同塑造方式、当代日本“批判佛教”、欧美现代禅学、近代中国佛学研究等话题,无不妙义纷陈,新见迭出。它的出版不仅如林镇国所说,“标志着汉语学界禅学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亦为当今汉语学界的思想史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普兰丁格的宗教认识论》,梁骏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6月,26.00元
《普兰丁格的宗教认识论》,梁骏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6月,26.00元
普兰丁格是当代宗教哲学的巨擘,问世于2000年的《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是集中体现其思想精华的扛鼎之作,也是一部从认识论角度为基督教信念辩护的名著。他在书中指出,近代以来对基督教信念的各种诘难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这信念在规范的意义上即是无效的;即使上帝“事实”上存在,基督教信念也只是凑巧“蒙”对了而已,不可能升格为对上帝的“知识”。
针对上述观点,普兰丁格以宏大的篇幅论辩说:基督教信念、至少就根据他的“阿奎那/加尔文”模型所概括的版本而言,是在规范的意义上得到“保证”(warranted)的信念。这一论辩的关键在于将“见证”(testimony)视为与“感知”、“记忆”同样具有基础地位的、为信念提供“保证”的源头,从而将基督教信念视为“基础信念”,而不是需要由其它信念加以支撑的信念。换言之,如果上帝果真存在,那么基督教信念就可以合法地享有“知识”地位――然则普兰丁格并未断言上帝“事实”上是否存在,他对基督教信念的捍卫,仅止于论证它是“得到保证的信念”。
作为对启蒙运动以来的主流认识论立场的一大颠覆,上述论辩思路不仅在专业哲学界内部引起了巨大反响,也对当今世界的宗教文化产生了深远的辐射作用。不过,理解普兰丁格的精深思想殊非易事,幸好现在有了这本由《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的中译者之一撰写的《普兰丁格的宗教认识论》,可谓金针度人。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美〕米尔斯著,周晓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39.00元
与其说作者是一位学院里的社会学大师,不如说他是一位十九世纪风格的左派知识分子。本书标志着他“像陨石一样横扫整个冷战美国”的开端,既回避了艰深的理论语体,也对现代学术规范所要求的访谈记录、问卷调查、数据资料等“知识底座”付之阙如,取而代之的是干净利落的叙述风格、广泛深入的文献研究和综观全局的历史视野。但书中的基本观点――中产阶级没有任何政治热情,只能尾随其它更有权力、更有声势的压力集团――显然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便提供了不少反例。
《政治的道德基础》,〔美〕夏皮罗著,姚建华、宋国友译,王世茹校订,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5月版,24.00元
作者在序言里自陈本书“是一本入门书,无须先有政治哲学知识方可阅读。它关注的焦点是政治合法性,这具体体现在功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社会契约论、反启蒙政治和民主传统等的不同理论之中。我对这些不同理论的讨论,旨在让读者了解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构成西方政治论争的主要的知识传统。”不过本书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出了普通入门读物的水准,其中涉及到的若干方法论问题在作者与他人合著的《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政治学应用批判》(中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一书中得到了更加深入的探讨。
《被冷落的缪斯》,〔美〕耿德华著,张泉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8月版,36.00元
本书中译本的副标题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然原文副标题直译应为“上海北京的中国文学(1937~1945)”。其间的区别并非微不足道,因为本书关注的毋宁说是在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心城市的上海、北京,文学场域在沦陷时期经历了怎样的“文化/审美”变迁;而不是在作为沦陷区中心城市的上海、北京产生了怎样的“国族/社会”型的文学场域。作者是夏志清的学生,本书的观点也容易使人联想起后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